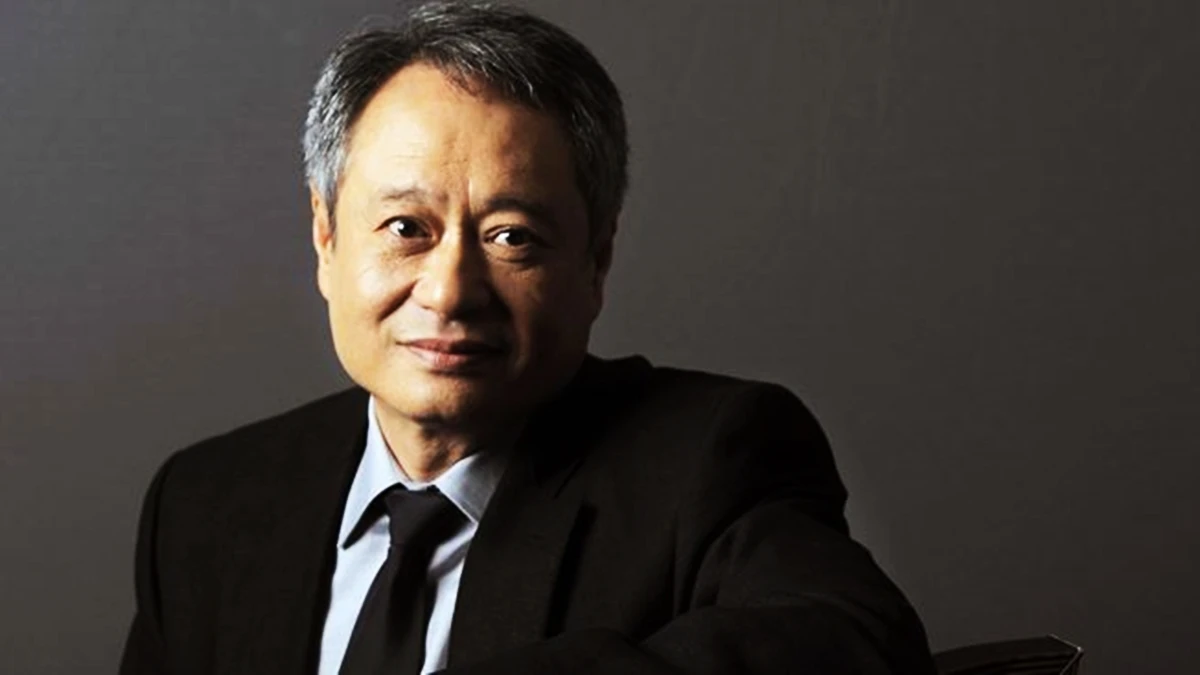陳文茜:中國男人通常不談自己的脆弱,但李安認為很多脆弱時刻,讓他找到了力量,看見了某些溫暖。為什麼你覺得脆弱對你那麼重要?
李安:大家看到我都是風光的一面,事實上,我經過很多失敗,脆弱是我的本質,與其說我的成功是從脆弱開始,不如說我很勇敢面對我的脆弱!我不在乎把它拿出來,也因為從事藝術的我有這種真誠,所以才會動人! 我小時候是個非常瘦弱、容易害怕、容易哭的人,從小碰到什麼事都要哭,對很多事很有同情心,但也因為我很瘦小,所以常常很害怕。我個子特別小,高中才過了一百六十公分。到了高中,我父親是校長,但我書也念得不是很好,本心是個很脆弱、很乖的小孩,從來不敢反抗。
不過,也不知道為什麼到了四十多歲以後,我竟拍一些別人不敢拍的東西,就是很喜歡! 太多的謙虛看起來會有虛偽的感覺。不過,謙虛是我的本性,不是我做出來的,有時我要很體面,因為想為台灣、亞洲人爭面子,這樣就能壯大自己的勇氣。我的本性是個很依賴人、脆弱、害怕的小孩,也很像台灣人的個性。有些台灣人從小到大都在輸的環境、害怕的狀況下長大,內心很脆弱,長大以後,也不是說要強硬,而是你的真誠不光是面對自己的脆弱,有時膽氣壯一點也是真誠的一部分,我盡量訓練自己,不要那麼怕。我一直拍到《斷背山》,我的第九部片子,才覺得其實我還滿不錯的。

如何面對自己
陳文茜:到了美國,一個讓你更脆弱的地方,用一種社會定義來講,你失敗了非常久,你怎麼慢慢找到了自己?
李安:自信有兩個方面,一個是天生的,這個我比較少;另一個是外來給的肯定,當大家給你的肯定多了,你自然就會產生「自己也不錯」的樣子,有一種自信心。我剛到美國時當然很害怕,比剛進台南的小學還害怕,因為語言不通。前兩年我都是半猜半聽,吸收非常有限,所以,後來我的視覺能力變得比較強,而我又很會猜英國人、德國人、黑人、白人怎麼想,也都猜中。所以,為什麼有人說我各種電影都可以拍,其實跟我很會猜有關,因為我很會觀察、猜測、揣摩、旁敲側擊,用各種方法抓到那個準頭,這跟那段時間的訓練有很大的關係。
陳文茜:很多跟你有類似機遇的人,認為自己懷才不遇,只有憤世嫉俗的面向,為什麼你沒有?
李安:我在生氣的逆境裡有時會找到同情,覺得如果不愛或不原諒別人,都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,生氣只是別人要做的事跟我們相撞,所以不應該有恨意。恨一件事情時,受最大傷害的其實是自己,不是所恨的人,所以生氣就可以了,不必做很激烈的舉動!我可以做的事情是「君子報仇,三年不晚」,很多仇我都報到了,但不是我自己去報的,是後來事實證明我正好有這個命。
陳文茜:當你拍西方電影時,相對比較堅強,因為你可以像「手術刀」一樣面對西方的題材;可是每一次回到東方,你不僅近鄉情怯,很多脆弱也一直跑出來,我很好奇,你一直在西方、東方間來來回回,為什麼東方或家鄉使你那麼脆弱?
李安:就像小孩和父母的關係四、五歲就決定了,因為你生出時是脆弱的,完全需要父母,力量的交流只有單方向,包括小孩對父母的需求、父母對小孩的管教,父母不給你喝奶,你就不行了。你那麼小,父母那麼大,他照顧你、管教你,所以,很多事情就會變得根深柢固,好像電腦晶片插在你的後腦,或者像機器人,放了一樣東西,你就知道「不能傷害主人」。
滋潤你、成長你的環境,不管是好的經驗、壞的經驗,都會深深影響你,逐漸變成我們心裡因素的一部分,你沒辦法選擇,也沒辦法抗衡,這也是我們最脆弱的一點。家鄉對我就是這樣,我沒辦法解釋我為什麼怕爸爸,等到我比他還要強壯、還有名時,我不但怕他,還怕傷到他的感情。也很難解釋我跟母親為什麼會有那些感覺,現在我對孩子也有那種感覺,對家鄉我就是會有這種情緒在裡面。

想對年輕人說的話
陳文茜:你這麼愛故鄉、愛台灣,在奧斯卡金像獎得獎時刻,謝謝台灣、謝謝台中,你會不會告訴年輕人,愈愛故鄉,不見得要留在故鄉,可以大膽走出去勇敢去闖蕩?
李安:我很害怕大家說「我很愛台灣」,其實壓力好重。不管是愛國、愛鄉,嘴巴講已經讓我覺得很不自然,因為愛家鄉是很自然的事,不需要講,你本來就會。拿出來講時,很可能是家鄉有問題,或是你有問題! 當初留在美國並不是計劃中的事,後來我出名了,回到台灣,短期間感受到很多愛,時間一長,也受不了,真的很難在這邊生活,因為我可能一條街都走不過去,大家都要找我照相,而我真的想做的事就是拍電影。我應該做的事在紐約反倒比較自由,可以創作,也有我的工作班底,而且紐約是世界的瞳孔,各地資訊都看得到。我既然在那邊建立了我的家、工作關係以及工作室,在那邊生活就會比較正常。我在台灣接受很多的愛,多到我自己也承受不了,所以我在外面生活,短期回來,像做主,又像做客,非常甜美,台灣人真的對我很好,通常到好萊塢或到奧斯卡都會受到很多本國人的敵意。
陳文茜: 我可能沒有講清楚,我其實很想鼓勵台灣年輕人走出去。
李安:走出去很好,因為台灣很小,是海島國家,本來就該走出去。在全球化的時刻,全球會更尊重你的地方性,因為你是特殊的。在美國有一句話說:「你可以把男孩拿到中國城以外,但你不可以把中國城拿到男孩的心以外。」台灣的存在可以具像,也可以抽象,這個世界很大,我們需要和外面學習、交流,互相幫助。

陳文茜:我們現在的年輕人面臨的大環境很不好,你在紐約蹲點那麼久,怎麼堅信自己的理想,不去選擇別人的價值?
李安:我們父親那一代在抗戰時期長大,經歷風雨變色,他們的憂患意識非常強,也有強烈的大中國情結,當然也有固執的一面,可是傳給我們的是生存力和韌性,也就是很能受氣、吃苦、有骨氣,我父親不喜歡我做電影,但他給了我一種骨氣,從小就告訴我們:「我們江西人很有風骨。」所以,我從小就知道人要有骨氣,但我沒有傲氣,外圓內方和生存力、競爭力這些都是他們那一代教給我們很重要的東西。
我看到台灣這一代的小孩,就比較軟一點,很善良、可愛,可是生存意志比較軟一點,有時你要提醒他們,擔心他們,但素質都非常好,善良又聰明。一個人會反映父母那一代,我們的小孩則反映我們是怎樣的人,而我們反映出的是父母,這個世界已經在變,台灣也一直在變,我希望台灣愈來愈好,生存意志和競爭力不要往下滑,光人好沒有用,要有生存力、競爭力,還要能表現。
陳文茜: 你在紐約等電影拍的那幾年,除了煮飯,你都在做什麼?
李安:我這個人有一個毛病,就是沒有做我喜歡的事,或者幫別人做事時,我整個人就好像塌了一樣,一點力氣都沒有,沒有辦法控制,這是我的弱點。我的性向非常清楚,覺得自己怎麼這麼久都拍不成,挫敗感很重。我太太她幫我最大的忙就是「不管我做什麼」,她有一種價值觀念是「不工作不可以」、「不努力不可以」。
其實我發呆的時間很多,我不鼓勵年輕人發呆,很多人發呆也沒有搞出什麼名堂來,怎麼交代?你沒有做事,又沒有做事的基礎,生活不知道該怎麼辦真的很糟糕,藝術其實是沒有理由的,賠錢、賠青春、賠你的家庭關係,各方面都賠了,但你還在做。

.jpg)
《我害怕.成功》
延伸閱讀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