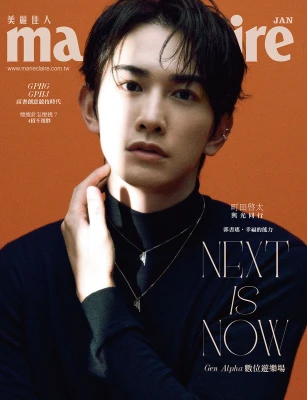部作品在威尼斯影展首映後獲得不少外媒討論,從敘事風格、影像語言到角色設計,都能看出她多年在影壇累積的觀察與細膩。不過,電影《女孩》雖然引起國際好評,卻錯過今年金馬獎入圍?背後究竟有什麼故事也讓許多觀眾好奇。此篇就整理出電影《女孩》的劇情重點、角色分析、影評觀點與沒有入圍金馬的原因。
舒淇從演員到成為導演!這是一場超過10年的旅程
早在《刺客聶隱娘》拍攝時,侯孝賢導演便曾對舒淇說:「妳應該也可以自己拍出一部作品。」這句話在十多年後成真。舒淇在2023年擔任威尼斯影展評審時,重新燃起創作慾望,並留在義大利完成劇本,她花數年構思、反覆修改,終於在2025年推出第一部長片。《女孩》由葉如芬監製、余景賓擔任攝影、張叔平負責剪輯,是一支實力堅強的團隊,她並未選擇安全或討好的題材,而是聚焦於1988年台灣家庭裡的暴力、沉默與代際創傷,這樣的題材不僅需要技術掌握,更需要勇氣與節制,《女孩》讓人看到舒淇作為導演的成熟面,電影不誇張、不煽情,卻能精準呈現壓抑的氛圍。

劇情簡述:1988年的台灣家庭,有的卻是靜默與崩塌
電影設定在1988年,正值台灣社會轉型時期,那是一個經濟開始起飛、政治逐步開放的年代,但許多家庭仍活在傳統權威與性別壓力下。故事圍繞一個住在老公寓裡的四口之家:父親蔣、母親阿娟,以及兩個女兒林小麗和妹妹,表面上是普通家庭,實際上充滿控制、冷暴力與恐懼。
林小麗(白小櫻 飾)是電影的核心視角,她懂得太早,也沉默得太久,每天放學回家,她聽見父親機車聲響就緊張,因為那意味著夜晚的暴力可能重演。母親阿娟(9m88 飾)在美容院工作,偶爾也在夜間陪客打麻將,生活艱辛又充滿無奈,她被丈夫長期家暴,但也在無形中把憤怒轉向女兒,用冷淡、苛責掩飾自己的恐懼,故事的轉折來自一位新轉學生李莉莉(林品彤 飾)。她從美國回到台灣,就讀同一所學校,性格外向、獨立、甚至有點叛逆,李莉莉帶著林小麗接觸外面的世界,也讓她第一次意識到「家」之外的可能,這段友情成為電影最柔軟的一條線,但同時也揭開了更多的傷口。

《女孩》角色介紹
林小麗(白小櫻 飾)
少女的成長與恐懼在她的眼神裡被完整呈現。白小櫻的演出沒有誇張的哭喊,卻能讓人感受到那種被壓抑的焦慮。她是全片的靈魂,也是觀眾進入故事的入口。
阿娟(9m88 飾)
這是9m88從音樂人跨足影壇的重要作品。她飾演的母親阿娟,是一個在婚姻裡被摧殘又無法逃離的女人。她有時冷漠、有時神經質,卻也在保護與傷害之間掙扎,角色不易討喜,但非常真實。
父親(邱澤 飾)
一個暴力、失控的父親,但導演沒有將他簡化成單一惡人。邱澤以克制的演技讓角色更立體,觀眾能感受到他被貧窮與權力壓力壓垮的疲態。
李莉莉(林品彤 飾)
她象徵另一種自由,讓電影從壓抑的家庭空間延伸到外面的城市。林品彤的演出自然、不造作,她的存在像一面鏡子,讓主角看到自己的被困。

每個畫面都彷彿讓人回到1988年的那個「家」
《女孩》的畫面由攝影師余景賓操刀,影像風格呈現濕熱、陰鬱又真實的台北。從昏黃燈光的樓梯間、嘈雜的美容院,到老公寓的金屬鐵門聲,細節都極具時代感,舒淇並未刻意製造「藝術片」的距離感,而是讓鏡頭貼近生活,觀眾幾乎能聞到空氣中的潮濕。並且與多數家庭暴力電影不同,《女孩》幾乎沒有「爆發性」的衝突場面,暴力被處理成日常的一部分,不靠配樂、不靠特寫,而以冷靜的節奏呈現,反而更令人不安。這種節制的敘事手法,使觀眾更能感受到暴力的循環與麻木。此外,電影中有幾個視覺段落特別受到外媒讚賞,例如:林小麗夜裡在衣櫃裡的夢魘場景,導演用螢光燈與塑膠布反光,營造出幾近窒息的畫面,沒有任何血腥或誇張特效,卻令人印象深刻。

描繪出「暴力」帶給家庭與世代的創傷
這部電影真正關心的,不只是暴力,而是「暴力如何延續」,母親阿娟雖然是受害者,但也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重複相同的壓抑。她對林小麗的苛責,看似冷酷,其實是一種錯位的保護:「妳不要像我一樣。」這句台詞在片中出現過好幾次,像是母女間無法說出的詛咒。舒淇的處理方式並不煽情,而是讓角色在矛盾中生存,她沒有讓阿娟徹底崩潰,也沒有讓小麗突然覺醒,而是透過許多細節描繪彼此的依存與隔閡,最終,小麗在成長後回望這段過去的方式,也成為電影的核心情感,結尾她坐在麵攤前吃麵流淚的畫面,外媒形容為「極為節制卻真實的收尾」。

外國影評的評價:「極為直接的方式拍出日常化的恐懼?」
外媒對《女孩》的反應普遍正面,影評談論道:「舒淇以誠懇的導演處女作,描繪一名女孩如何在貧窮與暴力環境中尋找反抗的力量,她的鏡頭冷靜但富同情心。」「《女孩》是導演的勇敢嘗試,她沒有淡化家庭暴力的醜陋,而是以極為直接的方式拍出日常化的恐懼。」以及「情緒節制、視覺強烈,展現新導演罕見的成熟」。當然,也有評論指出節奏偏長、剪輯略顯不穩,時間線交錯讓部分觀眾難以掌握。不過整體而言,影評普遍肯定舒淇的導演潛力,認為她的觀察角度細膩而真誠。

《女孩》為什麼沒入圍金馬?
許多觀眾看到威尼斯好評後,對《女孩》未入圍金馬感到意外。監製葉如芬在訪談中坦言:「金馬報名截止是7月31日,但我們8月15日才剪出第一版。因為威尼斯影展在9月,我們是壓到最後一刻才完成。」她也補充:「如果把一個還沒完成的版本送審,我會很難過。」舒淇本人也笑說,電影完成後她還想「再剪一個版本」,但上映時間已定,只能放棄,可見這部片在後製階段經過極多調整,錯過金馬報名並非忽略,而是製作進度無法配合時程。

電影《女孩》的隱喻與社會意涵
《女孩》雖以家庭為主題,但其實也是一部關於社會轉型的作品。1988年的台灣正在開放外資、引進西方文化,電影裡的李莉莉便象徵這股外來自由氣息,她的到來讓林小麗開始質疑家中秩序,也讓導演藉由青春友誼對照出社會的變遷,電影另一個重點是「女性如何被教育成沉默」。阿娟在職場被客人輕佻觸碰時只能苦笑,回家後卻把怒氣投射在女兒身上,這不只是母女的故事,而是一整個世代女性的生存狀態。

舒淇的處女作好評不斷
《女孩》讓人看見舒淇的觀察力,她並未追求影像實驗,而是以寫實取勝,鏡頭裡的空氣、濕度與光線都準確控制,表現出她對台灣生活質感的熟悉,這種「貼地而冷靜」的視覺風格,使電影雖沉重卻不流於矯情。舒淇在訪談中提到,自己在寫劇本時同時構思了幾個不同的故事。她笑說:「我不知道下一部會不會拍,要看《女孩》的口碑。」以目前國際反應來看,她未來繼續執導的可能性相當高。同時《女孩》這部電影,也讓舒淇成功讓觀眾相信,她不只是演員,也是一位具思考深度的創作者,她用鏡頭把那些無法言說的經歷重新排列,讓沉默變成畫面,這部作品也讓國際影壇再次注意到台灣電影的細膩與深度。
延伸閱讀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