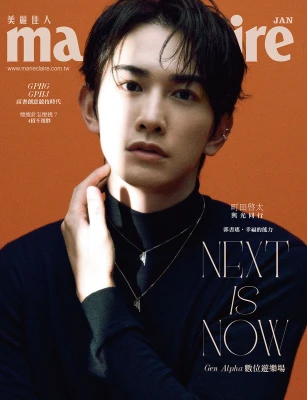當人們愈喜歡〈善變的女人〉這首詠嘆調,看演出時愈容易陷入道德矛盾當中,這也是《弄臣》最令人不安之處。唱出這首〈在佳麗群中〉的,竟是萬惡之源曼托瓦公爵,其男高音迷人美聲的外在魅力,卻是用來表現內心的邪惡放蕩;反倒是觀眾同情所寄的弄臣,卻主要以直白的自由吟誦表達。威爾第幾乎是希望觀眾不要像吉爾達一樣,能抵抗得了風流倜儻的情聖炫惑 ─ 但,這可能嗎?
弄臣的道德矛盾
《弄臣》改編自雨果著名戲劇《國王的弄臣》,而雨果原劇在1932年只演了一場就被禁,直到將近20年後才在威爾第的歌劇裡借屍還魂。雖然劇中法國國王被迫改成了義大利貴族,但批判的威力不減。這位公爵是唐.喬凡尼的傳人,在劇中像風一般勾搭了4位女性,從貴族人妻、純情少女到煙花女子,幾乎來者不拒。但是,威爾第沒有給他唐.喬凡尼那種直面地獄的勇氣,反而致力描寫整座宮廷的淫蕩,擺明是要掀起觀眾的階級仇恨。威爾第曾自白說:「公爵輕浮、放縱的個性是根本的禍源。是他引發了弄臣的恐懼、吉爾達的愛火及其他的一切。」
公爵又俊又壞,與弄臣看來是天作之合:俊俏的反派和醜陋的好人,這種極端對比是浪漫主義的最愛,可參照雨果的另一名作《鐘樓怪人》。不過弄臣並不像鐘樓怪人那般善良無辜,他其實是公爵作惡的幫兇,這才是真正考驗觀眾道德底線之處。看他如何助紂為虐,實在讓人怒火中燒。他自己的女兒被劫掠乃至背叛,堪稱罪有應得。然而,當他對觀眾傾訴人在江湖的痛苦,恐怕許多身為螺絲釘的上班族,也會心有戚戚。當你愈同情弄臣,就愈對他的惡行難以苛責,我們與惡之間,也就愈來愈難保持距離了。

弄臣的考驗來自內在性格的分裂:「他以奸佞之道指導國王,又以美德之道養育女兒。結果一個毀滅了另一個。」(雨果語)這就是為什麼威爾第要說,「弄臣是一個莎士比亞式的角色!」他真正的悲劇來自女兒吉爾達。單親父親管得愈緊,女兒逃得愈快,這應該是亙古不變的定律。吉爾達發現公爵是個感情騙子之後,還要以命贖愛,純情到簡直不可思議。但這種單純,可想而知是封閉式教養造成的。也可以說,這種憨呆是弄臣造成的。但更合理的解釋是,吉爾達唯一的情感寄託破滅,與其說是替心上人抵命,不如說是尋求一死解脫。
奢靡荒蕪的義大利電影風格
有紙醉金迷的奢華場面,又有窮街陋巷的扭曲愛情,《弄臣》放在任何時代似乎都能成立。例如:2013年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版本,導演 Michael Mayer 將場景設定為賭城拉斯維加斯,歌舞綜藝穿梭往來,對比娛樂事業底層的醜陋。2022年米蘭史卡拉歌劇院的版本,導演 Mario Martone 則設定為當代豪門,弄臣根本是個寄身上流的毒販。這些處理都產生了逼真的當代感。
這次臺中國家歌劇院邀演的版本,由澳洲導演 Elijah Moshinsky 在1991年首演的製作,卻絲毫不過時。場景設定宛如進入1960年費里尼《生活的甜蜜》中的花花世界:男性痛飲狂歌、女性爭奇鬥豔,名流時尚的奢靡享樂與荒蕪內心的對比,也和費里尼的電影一樣強烈。弄臣每每回到角落的梳妝台,上妝、卸妝,赤裸裸表現出人前人後的反差與蒼涼,有效地增加觀眾的認同。

全劇利用旋轉舞台,場景轉換令人目不暇給。一離開公爵的挑高豪宅,無論是弄臣寄居的公寓、殺手窩藏的旅店,都以雙層樓閣和室內樓梯、外牆爬梯,來造成空間切割、內外併陳的多焦點效果。第一幕弄臣的家裡,父親在和女兒懇談,隔壁卻是女僕在做菜、情人在爬牆。第三幕的旅店,公爵高歌〈善變的女人〉時,弄臣和女兒從街上駕車抵達,在門外偷聽;屋內的一樓是殺手在備酒,二樓是妹妹在豔裝打扮,為接下來的經典四重唱〈世間最美麗的少女〉鋪墊高潮前的柴火。這些豐富的細節,宛如細膩地轉入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的風格。《弄臣》的核心衝突,就是公眾形象與內心世界的衝突,以及迷人歌喉與殘酷現實的矛盾,而這也是它歷久不衰的祕密。
如何搭建一個能收放自如的舞台世界,讓每個聲音與細節都能盡情綻放,是《弄臣》最動人、也是最艱鉅的挑戰。今年十月,讓我們一同走進劇院,見證這齣歌劇如何在華麗與殘酷之間,燃起最撼動人心的火焰。
延伸閱讀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