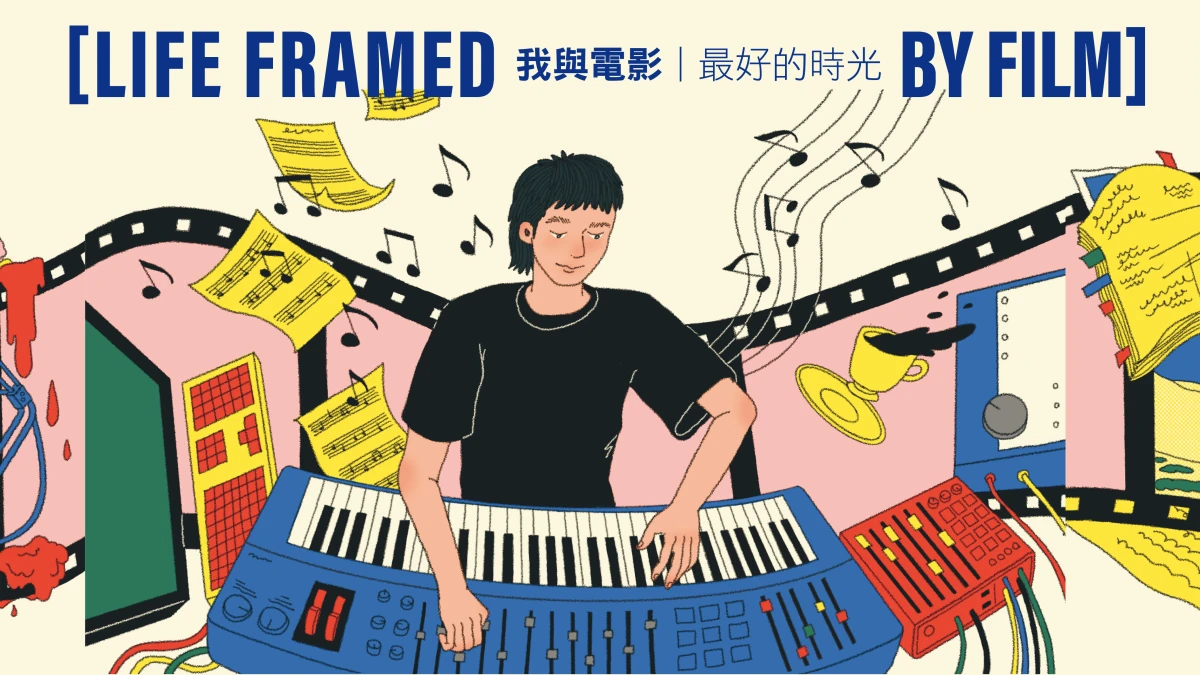隨著11月金馬獎頒獎典禮登場,我們邀集來自電影幕後不同領域,由業界推薦的傑出工作者們,分享電影及他們的人生。包括電影核心的導演及編劇潘客印,鋪陳畫面的電影攝影師陳克勤、美術設計梁碩麟,一些少見的職業如動作設計洪昰顥、特效化妝儲旭、親密指導林微弋,還有聽覺呈現的電影配樂盧律銘、聲音設計杜均堂。並邀請插畫家顧萱,將這些工作的場景與身影,以流動的畫面形式呈映在我們眼前。

數學系畢業後,盧律銘深感自己無法走上教書的道路,為了以音樂為業,他以寫譜能力申請上英國的電影電視配樂研究所。2011年回臺後,花了七年的時間尋找契機。從姊姊執導的長片《接線員》(2016)開始,到《返校》(2019)被看見,關於電影配樂工作,他說:「我的音樂是商業與藝術之間的橋樑。」
在任何容器中不改變本質
「一開始藝術性比較重,強烈地想要有稜有角,等待機會做類型電影配樂。」他舉例《返校》,以奇怪的管絃樂演奏方式,用盡力氣從傳統恐怖片手法中突破。直到商業片《消失的情人節》找上他,歷經長時間的痛苦與調適,完成後大家都很滿意,他感覺天線好像打開了。儘管音樂型態不一樣,朋友也聽得出來是他做的。「以前會期待稜角遇見剛好扣合的形狀。後來希望自己是液體,遇見任何容器都可盛裝,但本質不會變。」
電影配樂與音樂創作兩者間,有著模糊的界線。一方面音樂與畫面結合要有化學作用;另一方面電影是共同創作,彼此的觀點與想像不同時,很可能互相干擾。如何做到超乎以上答案的鋪排是最可貴的。這時候導演是調和的重要角色,只有他知道自己的電影要的是什麼,或者不要什麼。「大家對音樂的喜好、形容都不同,每次都是不同的挑戰,現在覺得溝通過程很有趣。」雖然也有疲乏的時候,對他來說人生都是音樂,就是最甜美的時光。

延伸閱讀:
故事總在結局後開始
著迷於電影魔力的他,喜歡在戲院感受前所未有的經驗,也在人生中一步步突破可能。「每部片我都會有新的嘗試,每一次嘗試都是在為下一部片準備。」例如從《返校》到《無聲》,他轉變以更精簡的配樂營造不安。《消失的情人節》首次嘗試的斑鳩琴,到了《瀑布》形成抽離的氛圍。一般弦樂錄法是扇形,在談論封院的《疫起》用長型直線式錄製,效果就像在醫院長廊一樣,「一百人中可能有九十八個人不會發現,但我後來將這個方法用在自己的樂團了。」
回望過去,他覺得自己是習慣追夢追不到的人,命運推動著他在實踐中成長。剛回到臺灣時曾有長片的機會,但導演辭退了他,跌到谷底後等待很久才重新開始,他卻也因此養成超越以往的配樂思維。
電影結束,片尾音樂響起。餘韻在正片看不見的地方發生。盧律銘知道當下不用太執著,意義慢慢會在日後浮現。
延伸閱讀:

電影配樂 盧律銘
英國 Kingston University Composing for Film and TV 研究所畢業。擅長用聲響營造氛圍,亦為電子與後搖樂團成員。多次入圍金音獎、三金(金馬、金鐘、金曲)並獲獎。曾以《瀑布》《返校》等原創電影音樂獲金馬獎。
──2025年11月號《美麗佳人》Special Report,〈音樂人生──電影配樂盧律銘〉
延伸閱讀:
- 我與電影,最好的時光|聲音設計杜均堂:「電影讓人們有機會彼此連結,產生更多可能。」
- 我與電影,最好的時光|美術設計梁碩麟:「這份工作讓我學會在混亂和壓力中,去信任自己的直覺。」
- 我與電影,最好的時光|電影攝影陳克勤:「幫助導演將故事影像化很有趣,每次都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故事。」
- 我與電影,最好的時光|特效化妝儲旭:「今天要比昨天更真誠、更真實,把恐懼留給假皮,把勇氣留給鏡頭。」
- 我與電影,最好的時光|親密指導林微弋:「對我而言,電影是我能想像最浪漫的存在。」
- 我與電影,最好的時光|動作設計洪昰顥:「唯有以自身的感受去創作,才能成為真正獨一無二的人。」
- 我與電影,最好的時光|導演潘客印:「電影讓我誠實面對自己,知道自己的脆弱和想望。」